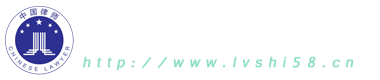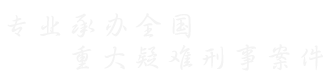一.吸收公众存款的数额
(1)吸收公众存款数额的认定与计算 根据最高法《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条第3款的规定:“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的数额,以行为人所吸收的资金全额计算。案发前后已归还的数额,可以作为量刑情节酌情考虑。”如果仅仅从字面理解,吸收公众存款的数额认定非常简单,似乎只要计算出吸收公众存款的总额就可以了,但是实践中所反映的情况却十分复杂。根据统计,在88起非法集资案件中,对于集资数额发生争议的有24件(人),其中被告人、辩护人的意见获得法院支持或部分支持的有13件(人),意见采纳率高达54%
根据统计,对于吸收公众存款数额的认定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①行为人所吸收的资金全额应当为实际吸收的资金 在实践中,行为人通常会与投资人签订各种名目的协议,在协议中约定相应的投资数额。但是有些情形下,投资人并未向行为人缴足其认购的金额,或者在协议中的返款数额中包含了预期的返利数额。司法实践中,曾有检察机关以协议中约定的返还钱款的全部数额认定,但是并未被法院支持。法院认为:借款协议书及借据上的金额包含了预期的返利金额,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作为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的犯罪,以被告人实际吸收的资金数额认定能更为准确地判断其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大小,做到罪刑相当,故依据投资人的证言、转账凭证、回单等证据,以投资人实际交款的数额认定娄某的涉案金额【(2015)朝刑初字第3283号】。
②投资人反复投资的数额原则上以投资的全部数额计算 实践中,经常出现投资人在获得全部反本付息款后,再次将资金投入,以期获得更多的收益。对于投资人的反复投资数额,司法实践中的认定存在一定争议:有观点认为,重复投资不应当累计计算,因为非法集资行为的对象只是单笔资金,如果反复进行计算,将会出现投资者的实际投入与集资数额不符的情况。另一种观点认为,重复性投资行为所涉及的数额应当重复计算,因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行为是对国家金融管理秩序的破坏。行为人每重新签订一笔投资协议,就是对金融秩序的以此破坏。从司法实践看,后一种观点,即:重复投资数额累计计算是主流意见。因为这种计算方式相对比较符合立法本意,且与司法解释中规定的吸收公众存款的数额计算方式一致[1]。
③认定涉案金额时应将利用利息转存部分的金额予以扣除 根据司法解释的规定,将被告人吸收的资金数额进行全额计算,不存在争议,但是在实践中,被告人吸收的资金数额巨大,吸收资金的周期也较长,因此会出现吸收大量数额的存款后,沉淀下的资金产生了银行利息等孳息。由此产生的孳息,由于不属于被告人所吸收的资金,因此在计算时应当予以减扣【(2016)京02刑终157号】。
④行为人自身投入非法集资项目的资金在司法实践中可以抵扣 在实践中,时常出现行为人不仅实施从不特定公众中吸收资金的行为,而且自身还参与其中的情况。相关行为人通常辩解自己投入的资金应当从其集资的数额中予以扣除,虽然有观点认为,该部分资金计算在涉案数额之内,理由是非法吸收存款犯罪是扰乱经济秩序犯罪,投资人不具备被害人身份,但是在司法实践中,行为人自己投资的数额也存在着抵扣的情形。例如:二中院在审理吴某上诉案中认定:商某投资的30万元与吴某无关,且一审法院未将商某投资的30万元及吴某自己投资的25万元计算在吴银安的犯罪数额内,因此原判认定吴某向曾某等24人非法集资的总数正确【(2015)二中刑终字第562号】。
⑤以回购贵重商品方式吸收公众资金的数额可以以投资人原购买该贵重商品的价格认定 在以商品回购方式吸收公众资金的,实践中行为人“出售”的 “商品”价值较为低廉,通常不具备再次交易的现实可能性,此种情况下,对行为人吸收公众存款的数额通常以其“出售商品”的价格认定,但是如果行为人以投资返利为由,以较低价格收购了投资人用高额价格购买的,具有较高经济价值的商品,并且将这些商品再变现出售给他人的。其吸收公众存款的数额,可以以投资人原购买价格认定。例如:朝阳法院判决的雷某某一案中:被告人雷某某伙同他人采取承诺定期高收益付款进而收购不特定投资人持有的投资型邮币类藏品的方式,向投资人变相吸收《错版珍邮》等投资型邮币藏品,上述投资型邮币藏品投资人共计花费人民币3000余万元购买。吸收的投资性邮币藏品已经被其出售。在审理过程中,雷某及其辩护人认为,吸收公众存款的数额应当以其向投资人购买此类投资型邮币类藏品的数额认定(400余万),而非以投资人原购买价格(3000余万)认定。但是其辩解并未得到司法机关的认可,法院认为:雷某收购的邮币类藏品,本身系投资人使用资金购买用于投资升值的有价值的资金载体,同时该载体的损失直接导致投资款项返还可能性丧失,向不特定公众吸收此类有价值的资金载体的行为,可认定为变相非法吸收公众资金,金额以购买价格确定,因此,本院对雷某收购的投资型邮币类收藏品,以投资人购买价格认定为非法吸收资金数额【(2014)朝刑初字第2069号】。
⑥认定具体的行为人吸收公众存款数额应当结合相关人员的地位、作用以及参与时间进行综合评判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件几乎均为共同犯罪案件,虽然共同犯罪中的行为人要对罪行承担全部责任,但是由于每个行为人在其中参与的时间、所起的作用以及地位均有所不同,这也涉及到对不同行为人涉案数额的认定上要有所区别: a.集资项目的发起者、组织者通常应当对吸收公众存款的全部数额负责,即使其在之后退出该项目或者仅仅在组织者之间约定终止项目而未向公众说明的,其仍应当对离职后或约定终止后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数额负责。例如:三中院在王某一案中认定:关于2008年12月11日后发生的数额不应计入王某犯罪数额的辩护意见,经查,被告人王某向果某、陈某提供了公司的印鉴及宣传资料,并授权果某、陈某以公司的名义对外融资,应对由此产生的危害后果与果某、陈某共同承担责任;王某与果某、陈某终止合作仅限于双方的口头约定,并未向被害人广而告之,更未采取诸如收回宣传资料、销毁空白合同和收据等措施,未能有效防止犯罪行为的继续进行;同时,无论是王某本人,还是果某、陈某均不能准确说明双方终止合作的具体时间,辩护人关于双方于2008年12月11日终止合作的辩护意见缺乏相应的事实依据【(2014)三中刑终字第87号】。 b.销售团队的负责人通常对其个人以及所带领的团队吸收的公众存款数额负责。例如朝阳法院在徐某某一案中认定:依照徐某某个人及团队成员吸收的金额认定其涉案金额,在此范围内,徐某某直接实施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行为并对团队成员具有完全的管理权,系此部分行为的主犯【(2015)朝刑初字第1386号】。 c.一般销售人员因其在共同犯罪中所起作用相对较小,通常仅应对其参与吸收的犯罪金额承担刑事责任。对此类人员涉案数额的认定理论上应当较为简单,但是因为种种原因,在司法实践中,曾多次出现由于对此类人员参与时间的认定不准确或者实施的具体行为认定不准确而导致涉案数额认定错误的情况。例如三中院在袁某一案中认定:在案投资人的证言、回购合同及相关辨认笔录能证明原审判决中认定的320余万元中的40余万元系其他业务员接待并签订回购合同从投资人处吸收的资金。袁某作为公司的业务员,仅应对其参与吸收的犯罪金额承担刑事责任,故该40余万元不应认定为袁某的犯罪数额【(2015)三中刑终字第00906号】。
⑦认定吸收公众存款数额的相关证据问题 第一,注重相关协议、合同、银行转账记录等书证对涉案数额的证明作用。 认定被告人吸收公众存款的数额原则上要以客观书证为依据。如果仅有投资人、中间人等证言证明涉案金额,没有相关书证印证的,由于难以证实证言的客观性,故对该部分数额应当排除。例如:在一中院审理的翟某上诉案中认定:因公诉机关指控翟某非法吸收王某某、许某存款的事实,只有投资人和居间人的言词证据,没有相应借款合同等客观书证或其他有效证据予以印证,法院认为不足以认定这一情节,应将该部分数额予以扣除。反之,如果书证等客观证据可以做到有效印证,即使行为人予以否认,则依然可以认定相应的数额。同样以翟某上诉案为例,该案中,翟某提出的公诉机关追加起诉的其他存款数额不应计入其犯罪数额的辩解。但是法院认为,公诉机关追加起诉的其他非法吸收存款,不仅有相关被吸收存款的投资人和居间人的言词证据,而且相应的借款合同、收据等客观书证予以证实;虽然这些借款合同、收据上没有翟国臣本人签字,但均盖有其公司合同专用章、个人人名章及公司财务专用章,与在案其他经王某居间介绍吸收存款的借款合同、收据形式上基本一致,同样应当计入翟某通过王某非法吸收的存款数额,故对于翟某的相关辩解,不予采信【(2014)一中刑终字第3336号】。 第二,不要忽视审查书证、审计意见等相关与认定数额之间的真实联系。 虽然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中相关账目、合同以及银行流水记录等书证所记载的资金走向等情况,通常而言是具备较强的客观性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完全以此为依据经行认定行为人的涉案数额。因为虽然书证等证据具备较强的客观性,但是在有些情形下,此类证据的关联性会存在问题。在有些情况下,虽然账目记载资金流入相关当事人账户,但这并不意味着当事人参与了集资之后的分红。例如,在二中院审理的倪某一案中,司法鉴定意见书中显示:涉案公司向该公司员工倪某个人账户汇入一笔大额资金,检察机关据此认定倪某参与了非法集资的分红,但是倪某及其辩护人提出,该笔资金系公司支付的购车款,支付购车款的原因在于兑现录用通知书中对倪某配备车辆的承诺。这一辩解得到了倪某录用通知书以及其他同案犯证言等证据的支持。法院最终确认了被告人的辩解【(2013)二中刑初字第1146号】。
二.退赔数额及认定方式 根据最高法《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条第4款的规定:“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主要用于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能够及时清退所吸收资金,可以免予刑事处罚;情节显著轻微的,不作为犯罪处理。” 根据调研发现,司法实践中确实较好地贯彻了司法解释的精神,对于能够退赃、退赔的被告人都给予了较为宽宥的处罚措施,对于能够弥补大部分损失的,甚至可以判处缓刑。需要注意的是行为人的退赔的方式,在实践中,有些行为人在得知司法机关对其进行调查后,为了避免被采取拘留、逮捕等强制措施,直接将自己的获利资金通过银行打回该公司的账户中。但是在审判过程中,司法机关并未认定其具有退赔行为。例如:在二中院审理的徐某等人案中,法院认定:徐某将个人非法获利中的600万元转回其公司而非主动上交有权机关依法扣押,导致该笔资金失控,不应认定为主动退赃【(2013)二中刑初字第1146号】。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虽然退赔是十分重要的量刑情节,但是如果退赔数额在造成损失数额中所占比重极小,或者非法集资行为造成其他不良社会影响,司法机关会将退赔作为次要情节考虑。例如:一中院审理的翟某上诉案中,法院认定:鉴于翟某到案后及庭审过程中能如实供述其主要罪行,认罪态度较好;且其到案发前后,退赔了部分被吸收存款,取得部分投资人的谅解,并退缴了部分赃款扣押、冻结在案,应对其依法从轻处罚。但考虑到翟某非法吸收存款的对象众多,多为老年人,且仍有大部分赃款未退还,给其余投资人造成的经济损失数额巨大,后果严重,在量刑时亦酌予体现从严【(2014)一中刑终字第3336号】。最终翟某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
三.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地位与作用的认定 在司法实践中,对于被告人在非法集资行为中地位与作用采用的是实质判断标准,即:以在集资行为中具体实际实施的行为为判断依据,而非单纯以相关的头衔或者职位认定。例如,三中院审理的韩某上诉案中认定:韩某虽然是涉案公司的部门经理,但同时也是涉案公司采取“渠道经济”模式经营后最早的加入者,领取了高管奖励,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不应认定为本案从犯【(2014)三中刑终字第596号】。 进行实质判断的依据,就需要证据的支持,特别是对没有明确职务的人认定主犯,更需要完整的证据体系予以证明。以三中院审理的杨某上诉案为例,上诉人杨某认为自己在案发公司内没有职务,仅仅是中间人,但是其辩解并未得到法院的支持,法院认为:杨某不仅参与了案发公司对项目的前期考察,亦在公司多次接待投资人,介绍项目和借款返利模式,带领投资人参观考察,范某还通过杨某账户向公司支付投资款等事实,显见杨某在本起事实中的参与程度和所起作用均已超出中间人的范畴,故其作为主要参与者应与范某就该起事实负同等责任;至于其在公司是否具备相应职位或者其本人是否对项目直接进行了投资,均不影响对其行为性质的认定【(2015)三中刑终字第00786号】。 当然,如果相应的证据之间存在矛盾或者瑕疵,不能做到相互印证的情形下,也不能仅凭借投资人的指认就认定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起核心作用。在三中院审理的罗某某上诉案中,就存在相关证据不能印证罗某某在案件中起到了核心作用:在该案中,虽然公司内部人员的证言都指认被告人罗某某是项目具体负责人,但是在对于罗某某具体职责的表述上却存在种种差别,不能取得一致。据此法院认为,被告人罗某某作为一名在各涉案企业的股东、合伙人、监事名单上都不存在的工作人员,要认定其参与了与银行的洽谈、有资金处理的决定权以及参与了项目的具体销售,证据并不充分,不能排除合理怀疑。被告人罗某某对其在本案中所起作用的相关辩解,酌予采纳【(2016)京03刑终322号】。
结 语 在当前的金融管理制度下,中小型民营企业的融资渠道是比较有限的,以至于为了真实的项目进行的融资行为,稍有不甚都有可能触碰刑法红线。在短期内,我们不可能要求国家对金融管理制度进行调整,但是在现有的有限空间内,仍可以通过研究司法判例,从而寻找到合法而有效的商业模式,去破解企业融资难的问题。
法律咨询点击进入www.lvshi58.cn 北京刑事辩护律师网(专注刑案,我们更专业) 全国刑事免费咨询热线18911845965
|